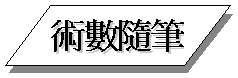 文•劉乃濟
文•劉乃濟 
悼方寛烈、慕容羽軍
接香港許定銘兄電郵,得知文壇好友方寛烈與慕容羽軍,同於今年九月五日及十日相繼去世。前者享壽九十歲,後者比我大一歲,今年八十七。生老病死,雖為人生必經的過程,惟是乍聞噩耗,仍不免黯然唏噓。
我在十八年前移民加拿大,數年後獲得入藉,以後每年都會回來香港探親。獲相交多年的作家林蔭、海辛、麥繼光等告知,他們每逢週日午間,都相聚在北角某酒樓與文壇眾好友見面談天。有著這樣好的聚舊機會,我當然欣然參加。以後,每逢回到香港,我都會去參加茶聚和舊友們見面。但近兩年便沒有再去,因為林蔭他們三位都已去世了,不想舊地重遊,免致觸景傷情。
就是在茶聚中,認識了方寬烈,我們很快便相熟起來,恍如多年老友。當時他主編《文學季刊》,邀我寫稿,每期都有刊登,而且發給稿費。有一期,我寫的那篇《廿世紀香港雜誌概況》,文長萬多字,他給予我數千元稿費。當時我覺得有些意外,因為這本書不是流行刊物,銷路狹窄,雖然得到藝術發局的贊助,但因編印成本重,每期都要虧蝕,支付稿費便要寬烈自己掏腰包了。有一次和他談起此事,他說稿費一定要付,是為了尊重作者付出的心血。
方寬烈出版過許多本書,看書名《香港詩詞紀事分類選集》、《郁達夫詩詞系年箋釋》、《漣漪詩詞》、《香港文壇往事》和《葉靈鳳作品評論集》等,便知道這些書的銷路極為冷門,不只不能賺錢,幾乎全是蝕本貨。他能夠「著書不為稻粮謀」,還可以在虧蝕情況下「屢敗屢戰」,全賴家族經營校服生意多年,在經濟條件上,可以讓他馳騁於文學境界。
我的媳婦是王亭之徒弟,他說方寬烈最近寫了一本書,叫做《靈界實錄》,記述他自己和文壇朋友對於靈界事物的所見所聞。方寬烈因為體弱多病,由王亭之襄助,完成此書。
今年初我回到香港,去過幾間大書局找尋此書,都說已經賣完了。我因急著先睹為快,只好打電話給方寬烈,告訴他買不到書。他問明我的地址,說會寄一本給我。當時,我覺得方寬烈在電話中的聲音很弱,不禁替他的健康擔心。過兩天,便收到寄來的書,還附著一張他親筆書寫百多字的小柬。我曾經在今年三月的本欄記述過此事,題目是「《靈界實錄》賣到斷巿」,想不到那麼快,便與此書的作者人天永隔。
慕容羽軍與我相識超過半個世紀,曾經在廣州《環球報》做過同事,那時我編經濟版,他編副刊。他原名李影,用慕容羽軍這個筆名寫小說和寫詩。廣州解放後,我和他在香港遇上了,他說想辨一本雜誌,但缺本錢。當時我得到在上環乍畏街布莊做掌櫃的叔父照顧,做棉紗布匹經紀賺了些錢,一拍胸膛,便拿出一些錢給他做出版雜誌的經費,還找到兩位也是廣州報界同業彭浪萍和何紹華來幫忙。他們當時找不到工作,終日流離浪蕩,當然樂意參加。因為付不起稿費,所有稿件,都由我們幾個人包辨。
那時候,辦雜誌要向華民司註冊,繳納擔保費一萬元,亦可找殷實商戶擔保。但有些雜誌結束了之後,沒有把註冊取銷,便把註冊租出來,我們便是租用這種註冊,來出版一本叫做《青春週刊》的雜誌,由慕容羽軍做主編。
此時,他們三個是居無定所,為了共同商量和工作,打算找個地方住在一起。那時候,青山道一帶都是菜地,有些高腳棚是菜農用來看守蔬菜的。他們便租了一個高腳棚作為居所,只是幾十尺空間,鋪上兩張草蓆,連床鋪桌椅都沒有。我本來住在叔父家中,也搬過來和他們共同甘苦。幾個寡佬自稱「青春四友」,這樣簡樸的生活郤不以為苦,躺在棚板上談天說地,想著明天會更好,自得其樂。
《青春週刊》太過文藝了,銷售的成績很差,出版了幾期,我的錢已經用盡,還欠下一些印刷費,「青春四友」迫得散夥。幾十年匆匆過去,我們日後各有成就。
彭浪萍在《真欄報》做娛樂記者,後來改行帶旅行團赴台灣。當時香港人去台灣要申請「入台證」,查核頗嚴,彭浪萍郤有門路。他有個全行皆知的綽號,叫做「喇渣和尚」,五十多歲便去世。真是一語成讖,他死時仍孑然一身,看來真是「和尚命」。
何紹華的頭腦最機伶,他跑金融經濟新聞,碰上香港股票炒得熱火朝天,報紙的經濟版最受讀者歡迎,郤又編寫人材最缺乏。他與徒弟組織一個團隊,專門承包編寫報紙的經濟版(《新報》是其中之一),賺到了大錢,後來攜眷移民美國。傳說晚年過得不怎麼愉快,因為與太太年齡相差很大,家庭紏紛不斷,他在美國憂鬱而終。
慕容羽軍在某大報做副刊編輯,一做就是幾十年,後來去了美國居住多年,又返回香港。在北角茶聚時,和他見過幾次面,可能是隔別太久了,而他又是個不多說話的人,幾次見面,我們沒有談過多少話。那時候,我已覺得他的健康不很好,因為說話沒有中氣。
「青春四友」中,三友已逝,頓覺人生苦短,也覺得自己幸運,可以多活幾天。(本篇完)